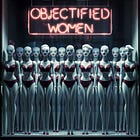人是社会性动物,这是心理学最基础的命题。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,人的主体性从未独立存在,而总是处在对他者的欲望、注视、回馈的不断塑形之中。我们与他人相遇、对视、交谈、连接,本质上是对「我是谁」的一种持续建构。
现代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形式的「连接」工具。从面对面的寒暄、名片互换,到社交软件上的点赞、关注和私信,我们的社交活动在媒介的推动下不断演化。然而,本质没有变化:我们想要被看到、被理解、被认可。而技术,只是加速了这个欲望的成形速度与强度。
线下社交往往带有身体性的存在确认,是通过言语、姿态、外貌等综合形象对自我的一次输出与被接收,是情感张力和身体在场的交互。线上社交则更加可控,可以修饰、剪辑、延时回应,更偏向于「展示」和「编辑过的自我」。
在这样的张力中,人们渴望一种「中间物」——既能快速有效地完成信息交换,又能在其中投射出个体精心雕琢的形象。
名片——无论是纸质还是电子的——就站在这两者之间,既是一种工具,也是一种象征。
传统名片曾经是商务社交中的标配。它的功能简单直接:告诉你我的称呼姓名、工作地点、联系方式,以及我能带来的资源或价值。除此之外,你对我其他的一切,比如兴趣爱好、曾经参与的项目、副业……完全不了解。
然而,随着网络、社交软件、AI 的普及和发达,承载单一身份的纸质名片逐渐被边缘化,只剩下在一些传统单一的商业场合中使用。取而代之的 iPhone 的 NameDrop 和各种社交媒体软件扫一扫添加好友。
在多元文化、跨领域的要求下,人们变成多面手,并且身份在算法和物化的影响下,也变得更加分裂——一个平台制作不同兴趣领域的分身账号,又或是不同平台不同领域。一会儿是探店达人,一会儿是摄影爱好者……
推荐阅读:
于是,One Card/Page 理念应运而生。
展示社交媒体的链接的这种「One Page/Card」概念也不稀奇—— Carrd.so 可能是我见过最早的展示个人社交链的网页。
对于我个人完整的显示内容,我更喜欢 Bento.me。它设计美观、支持网站预览,和自定义封面图的上传。如果只是想更方便、简单地策展自己的产品,那 Walling.app 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
海外 最火 的平台非 LinkTree 莫属了。LinkTree 从「社交信息入口」演变为「创作者的轻电商平台」,帮助创作者在一个页面中售卖课程、展示社交链、推广商品、建立联系,完成身份展示到商业转化的全链路。
《当代零售》(ModernRetail)是这样 报导 的:
Linktree 合作伙伴和业务开发高级副总裁 Lara Cohen 表示,目标是减少消费者购买创作者推荐产品所需的点击次数,从而提高转化率。
这也意味着,名片不再是一个联系方式,而是一个平台的入口。